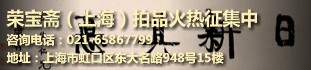推薦文章 > 異鄉的印記與故鄉的追問
異鄉的印記與故鄉的追問
――評胡慶魁散文集《在海之南》
李艷
對于一個他鄉游子,故鄉意味著什么;對于身處家鄉的我們,他鄉又是怎樣的所在,閱讀散文集《在海之南》也許會讓人找到答案。由南方出版社出版的胡慶魁散文集《在海之南》立足于此,作為生活在海南的異鄉人,他以獨特視角、獨到的表現方式和深沉的思索,將這里的山水風物、美食意象、人情悲歡悉數描繪,將祖國第二大島的景色與風情一一呈現在讀者眼前。當然,這里更是作者心之所愛,夢之所向。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思戀故土、追問過往、記述生活、感念生命,于幽微之處彰顯出濃濃情誼。
作者自稱“永遠的海南粉絲”,從整部散文集中不難看出,其對海南的深厚感情,以及因這份熱愛而衍生出的對依稀往事的眷戀。
《夢在海南》記述了八十年代期間,他從廣東海安坐上一條小木船和一群年輕人“偷渡”到海口的故事。“我在海口短短三天的一瞥,從雖然顯得破舊,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城市,從一張張年輕面孔上的激情演繹,從他們的期盼和向往中甚至勾畫出我在海南的未來,從此便在心中茁生海南情結,夢中總有椰樹的搖曳,海浪的撞擊。”正是這匆匆一瞥,便似乎得到了某種神抵般的啟示,終于有了1993年入籍海南的夢的實現。《人性的椰樹》更是表達了作者對海南細微景物的關注和情有獨鐘。“那年我從秀英碼頭一上岸,你那如鷹的風度、似松的骨氣就深深迷住了我。從來沒有一棵樹令我如此鐘情。你的神奇、美妙、冷峻、莊嚴,令人震撼和陶醉,一種說不清但卻十分執著的心動一下子攫住了我。我站在你身下,仰望著你,在那一剎那,決定了我后半生將與你為伴”;“我多少次在你的面前駐足凝視,仿佛覺得你是一首充滿抑揚頓挫旋律的詩章,深邃幽遠,蕩氣回腸。你的葉片揮舞,颯然有聲,你的心曲的表達既簡明通俗又激昂飛越,有如一個人,一個民族,在飽經滄桑、歷經磨難之后,取得成功、勝利或者輝煌的時候,那種悲喜交織而發出的真誠激越的心聲。”作者筆下,椰樹不僅是生命的展現,更是情感、溫度與精神的象征,與人的心性品格相得益彰。《東寨紅樹》是作者于春天時走進海口北部東寨港,親見50公里、面積4000多公頃的我國第一紅樹林保護區時的所思所感。“在氣象萬千的植物世界里,紅樹林既是極盡浪漫的歌者舞者,更是不畏艱辛、以苦為樂、甘于奉獻的勇敢者。億萬年來大海的波涌浪擊,日日夜夜、周而復始的潮漲潮落,既砥礪著又催生著紅樹林。紅樹林,這個永不凋萎的海上綠色長城,給了人類多少恩賜、多少啟迪!”《西沙土(外三章)》中既飽含著感性體驗,又蘊藏著理性思辨,通篇彰顯著作者的人文觀照。西沙島的沙是獨特的,雨是珍貴的,一些樹是官兵們像運泥土一樣運上去的。作者通過親身體察,對 駐島官兵日常生活進行細致入微的描述。別樣的風景造就了別樣的艱苦,也成就了“愛島守島建島”的西沙精神。
作者不僅與海南的景致身心相依,更對饕餮美食和秀色可餐的美味頗有心得。“在海南的吃,記住一個字就得,鮮!把住一字,你便會知道“吃在海南”絕非誑語也。”若有讀者初到海南,便可將《蓋了帽的海鮮》《風靡香港的文昌雞》《上了北京天橋的海南小吃》等幾篇美文捧于手上精讀一番,不光能體味其散文結構的凝練、敘述的精妙,在了解和搜尋當地美食過程中也不失為一種遵循。
說起苗族與黎族,浮現于眼前的是少男少女的環佩玎鐺和他們服飾圖案的花團錦簇,那種集織、繡、挑、染等傳統工藝技法于一身的美麗衣衫,如流光溢彩的星辰將夜空點亮。然而作者并非把注意力聚集于讀者通常會關注的衣裝服飾上,而是另辟蹊徑,將這兩個聚居于海南的少數民族進行深入探究,并最終推舉出一茶一酒作為各自的代表詳細闡釋,讓讀者盡情領略它們濃郁的飲食文化特色。“提起萬花茶,人們就會聯想到苗家人的熱情好客、用萬花茶待客的習俗。萬花茶風味獨具,喝一口,清香沁人心脾,余馨經久不散”;“三天后,朝下的竹筐尖部開始往筐下的陶土罐子里滴出漿水,這就是山蘭純液,呈乳白色。”從萬花茶、山蘭酒的幽遠歷史到原始制作工藝,作者層層解析、娓娓道來,不動聲色地向讀者展現苗家與黎寨的風情。
在海南生活了多年的作者,早就且把他鄉作故鄉。其不惜筆墨地為這里的人情風土感懷,心中更是沒有一刻不為遠去的故鄉和夢里的親人魂牽夢繞。這是時空流轉、空間變幻產生的神奇效能,在異鄉的土地回首過往、遙望來路,不禁對故土、對生命、對親人產生了距離的凝視,體悟到別樣的感觸。
濃濃的鄉音接續響起,從前的故土重現眼前。散文集中不少篇目涉及對往事的捕捉與回顧,充盈著作者對昔日生活的無限眷戀,以及對家人的不盡深情。
《在海口回望故鄉的年》中作者憶起兒時在家鄉鄂西過年的情境。從臘月里家家戶戶的忙碌,到正月里闔家團圓的歡樂,作者以孩童的視角,將那段記憶深處的美妙過往描繪得細膩生動。縱使相隔千里、光陰流逝,也無法取代家在一個他鄉游子心中難以割舍的特殊地位。故而“回望”便成就了他鄉與故鄉的某種聯結,成為超越時空的見證。鄉親臉上的笑意;無法想象的年夜飯的漫長;在父親的帶領下給先人上燈,印象里總是會下雪的夜,不是雪花,而是一粒粒的雪渣;雪渣在屋瓦上更加熱烈的舞蹈;小孩子吃得鼓鼓的肚子……故鄉的年帶著獨有的儀式感,在作者腦海中回旋纏繞,散發出經久不息的香氣。作者不由得感慨,“旅居海口十三年,印象里與年有關的,就是解放西路東邊街巷里寫春聯、賣糖果和炒貨的,弄出的一些淡淡的年味兒”;“我的故鄉過年很像過年。”
除了對故鄉的回味,散文集中涉及母親的至少四篇有余,足見作者對親情的無比珍視,對母親的深切懷念。
《花梨樹下》講述作為兒子的作者將花梨木屑拌水,為母親洗腳的故事。母親對花梨樹的喜愛;作者用一盆懸崖式博蘭盆景與朋友交換所得的花梨木屑;將要為母親洗腳時,她手足無措的神色;母親“人不如樹”的嘆息,雖為生活中平淡瑣事,但作者以花梨樹為牽引和依托,使兩代人之間的相互體諒與濃烈情感不斷升華,將彌足珍貴的母子之情呈現給讀者。《母親的手》則充滿兒子對母親的疼惜之情。“每年北風起時我會想起母親的手”;“母親的手是一雙凍手”;“母親的手更是一雙巧手”,作者通篇用質樸深摯的語言,通過對母親雙手的描摹刻畫,將勤儉良善的母親形象躍然紙上。母親的美麗不盡相同,但母親的溫暖必將成為所有孩子永恒的依戀――這是作者對親人和親情的詮釋。
曾經的往事如昨日般清晰,像老電影的回放歷歷在目,作者將其一一梳理記述,成為散文《陪伴母親》。35年前,17歲的作者神氣活現地穿著新軍裝,和母親在村口柳樹下依依惜別的情形;75歲的母親在電話里對兒女略帶幽默的責備;和母親一起對兒時往事的追憶,作者用最簡單地陪伴,渴望著對母親更長久的守候。行文情感充沛,細膩真摯,借庸常細微之事道出親情真諦。《送母親遠行》則是作者與母親的告別之作。母子連心,縱使天涯海角,千里阻隔,也無法將自己的根剪斷,于是作者發出“母親的走我是有預感的”感嘆。在海口美蘭機場過安全門時,母親的回首一瞥;在彌留之際等來歸家的孩子時,臉上漾出的笑意;母親平靜地離去,就像勞作歸來,衣服上的草籽兒還未來得及撣掉;在鄂西的土地上,在母親的衣襟下,跌跌撞撞走進人生的孩子,作者通過細微的觀察和對細節的描述,將與母親心心相印的情愫推向極致,足見筆力之深厚,感情之真切。
《纖道上的我》《放牛的日子》等篇目通過對兒時往事的抒寫,將對家鄉的眷顧之情娓娓道出。少年時代歲月的艱苦、生活的貧乏,反而使無憂無慮童真的天性與頑皮得以充分釋放,成為多年后身處異鄉的作者無法忘懷的追憶。“那時的我還沒有讀過屈原,也沒有讀過沈從文。待讀過后才知道,我背纖的地兒原本也是生長著芷草、蘭香以及山鬼和云中君的。何以對這些美麗與神秘一點印象也無?”“當我從生命個體的感受轉向社會的歷史的思索,我發現,纖夫面對艱難困苦的從容和那種竭盡全力的一往無前不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特有的精神,不就是這種精神五千年來一如既往地推動著中華民族前進的腳步!”“憶起我童年的牛,曾給我歡樂的牛,此刻的我,也似那頭不堪重負的老牛,眼中盈滿了淚水。”
有關故鄉與他鄉、向往與懷念、剝離與找尋的話題,已如宿命般不可逃脫地既追溯著過去,又企盼著未來。在胡慶魁筆下,故鄉與他鄉早已渾然一體,凝聚成無數的牽絆與懷戀,幻化為對生命的體驗和感動。無論身處何處,不忘來時之路;不管與多少人相遇,依舊感念故人,這便是散文集《在海之南》里作者對他鄉的深情和對故鄉的深意。
(作者李艷,天津市作協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