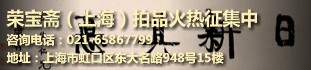國畫符號語言的當下解讀 ―― 張永山
摘要:本文以求從文化精神到中國畫的符號特征上解讀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意義,使現代中國畫在創作實踐上有一種方向定位,而從“古法”之中求取“今法”的文化認同性,以榷正符號語言的偏廢之歧誤。
關鍵詞:國畫,符號,當下解讀
中國畫自隋唐宋朝達到繪畫本體語言臻于完善的藝術高峰,同時也逐步開始形成符號化語言的程式體系。隨著宋尚法度的繪畫(院畫)達到巔峰,以北宋中期的蘇軾、文同、米芾等為代表的文人畫家,不滿于畫院畫風,從而出現了文人畫流派。他們重理想人格精神的表現和抒發,注重詩、書、畫(印)融合一體的人文精神理想的主體張揚,以相對簡的“符號”切合于詩書畫的尚意精神,使“天人合一”的文化哲學觀念,更趨于發揮符號的程式性表達,從謝赫的“六法”衍化為劉道醇的“六要”、“六長”,而突出了氣韻、筆墨、簡淡、形成的一種風氣,而重寄興、自娛、見士氣、逸氣,以寫代畫,因此符號化的概括語言由此而生,并在之后日臻完善。
一、中國畫符號語言的來源和完善。
1、其實,中國畫的符號語言,并非到宋元文人畫產生興起時才出現,自遠古時代,先祖對自然、天、地、水、火、木、金、土的認識,做為一種觀念文化精神象征,注重順應自然法則,遵循并崇拜自然的傳統,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字符號,群體圖騰、低級圖騰,從轉型中的共識性和人們在大量的原始彩陶所刻畫的日、月、星辰、山川、動植物圖形符號中可見中國畫符號語言的來源基礎,而春秋戰國之后的“天人合一”的儒道觀沉積而成的《周易》的民族文化精神,就是“天人同構、時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易道”構成了中華文化最穩定最本質內核,決定了中華文化的面貌特征和總體走向,符號語言標示出了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結構和文化審美屬性的價值取向。這種悠遠的深層的本體意識,使中國畫進入宋元朝之后的文人畫階段的符號語言特征,更加具有文化特色和體系性,它的發展和完善到元明清代更進一步得到發揚。時值今日,在現代西方文化價值大潮的沖擊之下,尤顯其鮮明的文化性和獨特的玄奧生命力。
2、什么是傳統符號語言呢?正如我們的漢字一樣,中國畫中人物畫的“十八描”、“山水畫的各種皴法”、山水花鳥畫的筆法(畫法)結構(書法中稱結體),如“竹葉法”的“個、介、分、重人字形”等;蘭花的“交鳳眼、破鳳眼”,梅花的“品字形”,其枝法“井字女字結構法”等等無一不為符號特征,山水畫宜如此,其樹法的“針葉、點葉、夾葉法”都是人們共識的明確沿用的符號語言,并且這樣的語言在人物、山水、花鳥畫中都有著共通性,人物的描法符號可通用于山水畫花鳥畫之中,又如游絲描可用于仕女人物肌膚也可用作花卉勾描之法,“枯柴描”、“折蘆描”也可用于花卉枝干的勾描方法和人物衣褶衣紋的勾描法,“行云流水描”、“折帶描”皆可用作山水的山石云水皴描法和人物紋飾衣褶的描勾筆法。這些都說明了中國畫的符號語言的通聯關系特征。再如山水畫中寫松、竹、梅與花鳥畫符號相同,只是大小之別,遠近之別、繁簡之別。在山水畫花鳥畫之中,點可表示多種意味,如落點于石上為苔點,落于山頭為樹叢、落在地上為雜草,落在山水坡角為碎石等,這些都構成了符號的具體又不具象的暗示表述方式,它可積點為線(輪廓)可積點成面(叢林草坡),而山水畫皴法表示肌理的豐富變化,也常用于人物皮膚及衣褶,而產生可感的效果,而又非全視覺上的直觀物象,因此成為具文化意味的符號書寫程式,它有著廣泛的共識性群體和個性特征,如吳道子的用線被稱為“吳帶當風”曹不興的線條人稱“曹衣出水”。還如山水畫中的“斧劈皴、披麻皴、豆瓣皴”法“拖泥帶水皴”等等幾乎是故名思意的固定用法,在歷代傳承用筆上又有明顯不同的個人特點而存大同,求小異。
3、自宋代以來,中國畫從蘇東坡,米芾、文同等文人畫家始到“元代四家”更是將山水畫,(花鳥畫)推向符號化的簡約,清逸的境界高峰。東坡以朱色寫竹,不僅在形色上以符號形式傳達興娛之性,也表明了文人畫的梅蘭竹菊松的“歲寒三友”“君子之風”的精神符號意義,故歷代文人寫而不易,經朝不衰,而當下的現代藝術家象征主義者卻沒能賦于其象征物以更深的寓義,而失卻在文化精神家園之外。其探求的目標不正是中國文人畫家所演繹的文化象征符號吧。因此,中國文人畫家的符號語言是可發展的,是切合于當下時代文化心理特征的。要保持文化的先進性,既要傳承傳統,又要與時俱進,改造傳統,化西為我,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二、符號語言的傳承與當下疑惑
1、符號語言的傳承性與現代性
做為東方文化的積淀和承載語言,符號如文字一樣明確而善深于表述文化含義,同時也適于規范傳承解讀,它并非完全為視覺沖擊效果的“純視覺藝術”,它在于把玩之中體味,它有著對人對藝的雙修特性,甚至還帶有禪宗修煉意味。在其語言的傳承特征上,山水畫(花鳥畫)在歷經元明清乃至今日,它的符號傳承意義都仍未改變,其符號自比興、寄情、自娛需要與之書法所然,其尚從的“六要”標準,即為:氣韻兼力,格制俱老,變異合理,彩繪有澤,去來自然,師學舍短,“六長即為:粗鹵求筆,僻澀求才,細巧求力,狂怪求理,無墨求染,平畫求長。”而將畫定評為:逸、神、妙、能四品,這就明確表達了語言的文化傳承定義。它不拘泥于以形傳神,而“筆簡形具,得之自然”,這就固定了其傳承和發展是一種共識的符號演化程式性。特別突出重于筆墨符號程式,由此弱化了實用教化功能和繪畫的純視覺性,走向“曲高和寡”達到詩書畫印的文化性的藝術高潮,開創了畫史的獨特地位,因此它的傳承是以古意為重,以范本畫譜所設定的法度為基礎,忌“邪、甜、俗、賴”把學與用的法度發揮至“無過無不及”的“中庸之中道”達到天人合一的不偏不倚。故不學古不行,筆墨不隨時代也不行。這就是它的傳承特征。其傳承語匯的來源其一為古人的歷史積淀,其二不斷從中改造,從自然中依據古法,得到新的創造,并被后人認知的共識符號,才具有了當代性。
2、符號的現代傳承中的誤讀和困惑
而當下現代文化認同的歧義造成了人們認識的誤讀和困惑,其中主要原因是對傳承語言失范,在人們的“西法式”寫生開發的“創造”過程中,使傳統符號語言和程式不斷式微化,其解構所帶來的困惑,而從西法中求其補充。而任意的杜撰符號語言,使新生代失卻了對傳統的文化象征的內涵解讀,甚而對傳統的生厭與逆反,而一味追求視覺效果。而另一方面,以懶代之,以所謂傳統面貌相因抄襲,失卻了在自然中以古法創造能力的培養,只種“一畝三分地”閉門造車成風,以為有所創造發明,凡此種種都有礙于傳承與創新的規范,不利于中國畫的繼承和發展。
結語:中國畫的符號語言體系是完整的系統,它的現代性在于從傳承中解讀和在自然中行萬里路的觀察體驗,以古法尋求創新機杼,從而才能繼承發展優秀的文化傳統,其現代性,應是在此基礎上,擴充符號語匯,加強視覺張力,以“中庸之中道”為度,轉換符號語言和筆墨程式的表述方式,生發新意,從而發揚光大,這需要代代傳承的深厚傳統功力,也要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以及很高的膽識探究創新的法則。要真正認識傳統,才能正確認識現代,走出誤讀,走向共識,化西之法,傳民族之魂,創中華之新精典,走出中國畫的符號語言特色的現代解讀之路。正象潘天壽先生所提出的:“凡事有常必有變;常承也;變,革也。承易而革難。然常從非常來,變從有常起;非一朝一夕偶然得之”,“常變之道,終歸于自然也”。
注:參考文獻:
摘自《宋人畫評》劉道醇原序云告譯注,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摘自《元代書畫論》鄭杓、劉有定《衍極》潘運告解注,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摘自《美術觀察》2003年2月張立辰、梅墨生撰《別立宇宙,同一吐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