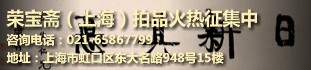情懷高古 氣象幽遠 ――造訪毛敏丘壑 覃國棟
山水畫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它的萌芽和興起與魏晉時期的玄學之風有著直接的聯系。當時的文人士族盛行隱逸山林、奇情山水,以獲得精神上的逍遙,竹林七賢便是隱士中一群有代表性的人物。這一時期也產生了最早的山水畫論,東晉顧愷之的《畫云臺山記》對畫山水作了一定描述。與顧同時代的宗炳所著的《畫山水序》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山水畫論,并成為山水畫的理論基石和核心,形成了山水畫的藝術精神。《畫山水序》的藝術思想為歷代畫家所推崇的關鍵,在于其所追求的是形而上的精神境界,這也正是畫家們的精神家園。
歷代山水畫家毛敏先生,生長于大西北甘肅省的臨洮。臨洮史稱狄道或洮陽,地處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接壤地帶,歷史久遠,文化積淀深厚,是古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的邊塞要術,也是著名的馬家窯文化的故鄉。颶風狂沙鑄就了毛敏堅強的意志,蒼涼雄偉的高原培養了他樸厚的性格,燦爛的歷史文化養育出他那藝術家的情懷。
毛敏先生天資聰慧,從小就與繪畫藝術十分投緣。由于他勤奮好學,不懈的努力,以優秀的文化成績和專業成績考入了西北師范大學美術系學習深造。畢業后,仍鍥而不舍,堅持深入研習國畫藝術,他最鐘情于山水,并沿著正確的道路穩步向前。
在西風仍然劇烈的今天,有些畫山水的人被吹得暈頭轉向,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家門,失去了最根本的東西,搞出一些怪誕虛空的形式,雖然嚇人,但搖搖欲墜。毛敏先生卻是以為頭腦非常清醒的山水畫家,他不僅沒有割斷與傳統的血脈聯系,反而更加深深地從傳統中吸取養分。他廣泛臨摹古代繪畫,認真研讀古代畫論,從中參悟妙理,以期得到精神涅盤。
毛敏先生更可貴的是,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他不斷地深入生活與自然對話, 長期進行寫生。入燕山、進太行、奔祁連、過青藏,每一次體驗和寫生都在不斷地加深他對山水的理解和藝術上的進步。記得一九九八年五月,我與毛敏先生隨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到河北省興隆大山區寫生。面對大自然,他不是急于去畫,而是在山間興游,感悟自然,發現美妙,尋覓物我交融之境。轉了四天之后,才開始動手寫生。他筆下的畫面透發出生生之機,人文情懷濃厚,人性化的自然發于筆端,躍然紙上,親切而和諧。寫生是他創作的源泉,大自然啟迪了他的只會和靈感,他以大量的作品來抒發藝術激情,穿鑿心靈與自然的畫卷。
造訪毛敏先生筆下丘壑,實在是一種心靈享受和精神自在。
胸中丘壑,靜里乾坤。艱辛的生活酈城,豐富的學養修為,深切的自然關照,使他能洞悉到生命在靜中的玄機與美妙。在人內心的最深處,靜才是真正樂土。他把心靈最美好的境界奉獻出來與人共享,讓人從丘壑中也能參悟到他心靈的平坦與恬淡。欣賞他的畫,相當于愉快的山水之游,雖歷經千山萬水,卻勝似閑庭信步,心平若水,趣味無盡。即使是他筆下的祁連山或青藏高原,也不會氣霸天下,橫秋千里,總給人一種閑適祥和之感。
感應八荒,思意宏博。古代道家修煉講究思接天地,神游八荒,追求天人合一之境。佛家講究參禪悟道,明心見性,修成正果。儒家則講究修身養性,遵循天經地義,中正立身。毛敏先生不是機械地描繪自然,他有較好的國學基礎和人文修為,有豐富的思想。在長期的繪畫生活中,他反復地思考過人生與自然的來你系,不斷地感悟自然,進行物我交融的精神思考,在創作中寄托精神情感。在他的山水畫中,當你透過山林迷蒙的氣息,會感悟到耐人尋味的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懷,一級那彌漫著的靜而又靜的禪意。
情懷高古,氣象幽遠,這應該是毛敏先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他算得上是一個西北大漢,可是他心靜如禪,全然一副文人學者氣度,這也許是他天性好靜。本性即佛,加上后天造化,心性合一。畫為心跡,形是山林,而神為人性人與自然合璧是為山水。他的山水畫全然是在氣定神閑的狀態下創作完成的,沒有絲毫浮躁之氣與風火之氣,平和優雅,意境照人,六合通幽。
心安自在,圓融無礙。毛敏先生面對滾滾滾紅塵和繁雜事態,淡然處之,始終保持心靈的清靜,毫無雜念和奢望。專心繪事,樂于山水之道,這無異于魏晉文人情懷和信徒的虔誠。山水的妙門也自然而然地為他慢慢開放,讓他步入更美好的藝術之境。
他的山水空谷可居可游,境界宜人,更可品味。我愛毛敏山水,敬佩他對山水的赤子之心,愿將心愛的詩作贈送給這位虔誠的畫家:
造化入妙理,
容顏出生機;
供養山與水,
常懷赤子心。
2006年6月于不二門山居
覃國棟——湖南湘西人,副研究員,著名青年美術史論家。